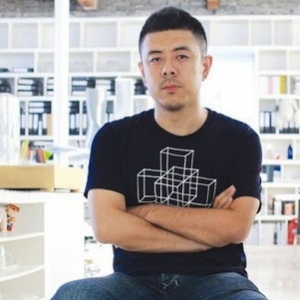|
摘要:日前著名建筑马岩松接受某媒体采访,马岩松,生于1975年,毕业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和耶鲁大学。2001年获得美国国家建筑师学会建筑研究奖金。曾在扎哈·哈迪德伦敦建筑师事务所和纽约埃森曼事务所工作。2004年成立MAD北京事务所。其为重建纽约世贸中心而设计的作品“浮游之岛”模型被中国国家美术馆收藏,作品还有梦露大厦、鄂尔多斯博物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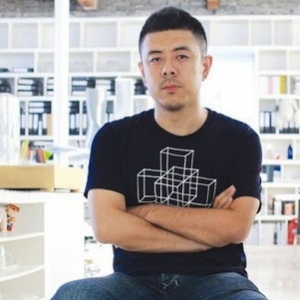
“现在中国的这些建筑全是又大又权威,整个现代的城市文明是权力和资本,不管是崇拜资本的城市,还是崇拜权力的城市,人都是缺位的,就这个城市不是人的”谈到为什么回国,马岩松说,因为中国建筑的问题出在方方面面。
他被称作“中标国外标志性建筑第一人”。2005年,30岁的他凭借“梦露大厦”的设计赢得加拿大多伦多的一次国际设计竞赛,一举成名。在国内标志性建筑多由外国人设计,而国外建筑罕有邀请中国建筑师的背景下,马岩松海外中标的消息显得有些突兀。
他是少有的时尚的、明星式的建筑师。他的年轻也被津津乐道,一句流行语是:“建筑圈30岁以前成名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是马岩松。”办公桌上那张家庭照里,两个儿子笑得眯起眼睛,马岩松杵在中间,一本正经。
批判是马岩松从回国起就一直在做的事。他批判他看到的一切:所有的法院都是大台阶上去,所有的政府大楼都在市中心,前面一个大广场;所有的城市都一个模式,一张规划图啪啪啪拷贝;所有的住宅一个样子:标准化、大批量生产、非人性。2004年,他将两年前创立于美国的Mad建筑所转移到北京。此后两年多,他的设计因为“过于前卫”,一个都没建成。
“发表那么多,你倒是建啊。”马岩松表情夸张、语带调侃地模仿着批评者的不屑。在他看来,建与不建只是时间问题,更重要的是,建筑师要有对美好未来的一个提案。“空想在中国是被嘲笑的,因为中国推行的一直是实用主义,从上到下,从黑猫白猫就开始。实用主义不适用于城市发展,因为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发展就像一部哲学、一个交响乐、一个伟大的绘画作品。”
他的建筑同时挑战着国内的施工水平和国人的审美。比如鄂尔多斯博物馆,不规则、曲面、金属,是一个巨大的异形建筑,用他的话形容,“一个飞船啪地扔在沙漠上。”他的解释是,希望剥离掉任何现代主义的东西,直接和沙漠对话。如今沙漠和戈壁已经被各种风格的“像建筑的建筑”城市化了,他的“飞船”突兀地立在那儿,非常超现实。不管进不进博物馆,总有人乐意在周围的斜坡上呆着。他挺满意。
近几年,他讨论的话题是“山水城市”,这个由科学家钱学森1990年提出的概念,20年后启发了马岩松。接下来这两年,体现这个思想的建筑就要破土动工了。在他的脑子里,山水、自然都不是一个传统文化的概念。“其实传统只是我们现在看的传统。未来是什么?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把所有没见过的东西都叫作未来感的东西,而已。”
这是马岩松式的敏锐、率真与自信,你同样可以在另一个关于他为什么回国的回答中看到这点:“所有有问题的地方我都感兴趣。”
央视大楼是帝国式建筑
问:你曾评价过央视大楼的设计,说是建筑师库哈斯看到了中国的现实,然后用一种比较粗暴的方式表达出来。
马岩松:我觉得这是一个跟中国权力的合谋吧,是中国的帝国建筑。整个城市化的这种建筑的初衷,跟这个帝国形象有很大关系。现在中国的这些建筑全是又大又权威,所有的法院都是大台阶上去,所有的政府大楼都是在市中心,前面一大广场,都是最大最豪华的建筑。这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整个现代的城市文明是权力和资本,在西方就是资本。不管是崇拜资本的城市,还是崇拜权力的城市,人都是缺位的,这个城市不是人的。按理说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是所有人要感到自豪的,但为什么好多奥运会建筑,包括CCTV这种标志性建筑大家都没感觉,说不上好看不好看,或者不好说。
问:或者也会觉得跟我没关系。
马岩松:因为它确实跟你没关系啊。它就是一个帝国式建筑、一个纪念碑,它横空出世表达出那种力量,是当时的形态、状态。我说句玩笑,后来这把火烧了都是必然的,没有那种目空一切的心理状态,他不会定这么一个方案,也不会去放违规的烟花,而且每年都放。
问:建筑师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马岩松:我现在说这话就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了。
问:批判者吗?
马岩松:我觉得建筑师首先是一个批判者。当然建筑师还得有更积极的一方面,你得有对更美好未来的一个提案。一个城市的历史和观念,与建筑和城市最后出来的形态是非常一致的。所以也许能有一种反作用。就是你的提案、你的建筑和城市设想能够成为一个开始,或者说能成为一个改变社会的契机。
建筑活动和城市形成是全社会所有人都参与进去了,我觉得建筑师是这些人里最接近知识分子的角色。工程师是管工程和技术的,决策人、政治家、资本家有他的考虑,只有建筑师是有可能站在一个历史角度去看这件事。如果他最后很悲哀地变成一个技术提供商的话,等于整个这个事没有任何文化上的考虑了。
其实包括批判和空想,都是建筑师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必然职责。
问:从梦露大厦开始,不断有人来找你,什么样的项目你愿意做?
马岩松:这跟我最早想回国就有关系。我觉得中国建筑问题是在方方面面的。比如说像很多新城区的城市化,都是在一个自然环境里直接规划一个城市,很多规划院就把一张图纸到处用,所以千城一面,所有城市都一个模式,这个模式从不考虑人文的、原来的自然环境这些因素。
从大城市到小城市到新城,要建很多文化建筑。但在中国,博物馆大剧院都变成一种奢侈品,或者是一个标志性建筑,或者是政绩工程,就是不让人去参与的。还有大的住宅,全国的房子,一个厅一个厨房一个餐厅一个卧室,进去基本上全都一样。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城市,追求利益、追求实用性。所谓实用性就是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然后就是非人性。
问:你觉得好的建筑是什么?
马岩松:我觉得建筑和城市是一个东西。一个城市就应该先有一个理想,尊重这个理想作为大前提,你照着这个方向走,它就是一个人性的城市。我为什么说山水建筑、山水城市,不就是整个古典中国的精神家园?就是人跟自然的这种关系,人在这个环境里去看自己的生命。它是一个精神上的追求,跟现在的绿色建筑完全不一样。绿色建筑还是技术上的东西,还是觉得我可以用技术怎么怎么样,它不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
问:你设想的建筑是在大城市的情况下依然是关怀人的?
马岩松:就是在大城市中让人跟自然有一种情感上的和谐。然后建筑不是建筑,建筑应该就是环境本身,就是一个环境体系。像一个园林里,很难去把建筑单拎出来,都是一体的。
问:东方式的?
马岩松:东方式的一个思想。现代的建筑基本是专业化的,建筑、景观、规划,都是分开的,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人在城市里生活是完整的体验,是一个系统,必须有一个整体的环境观。
我不想贩卖中国人的身份去谄媚西方
问:你也希望能在国际上说出你的想法吧?
马岩松:我觉得梦露大厦是一个偶然,但也偶然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到来,就是中国青年一代的建筑思想可以有它的价值。
现在中国建筑好像挺被关注的,但其实关注的点是在中国的城市化和中国难以置信的繁荣上。很多关注里都包含着批判,包括普利兹克奖,都是对中国城市化的这种批评。
如果西方主流文化对中国建筑师那么喜欢的话,为什么不邀请你去设计他们的国家博物馆和国家大剧院?对吧。所有中国国家级文化建筑全是国外建筑师设计的,好像中国建筑师都没法了解自己的文化。然后外国文化界对中国这么感兴趣,也从来不邀请中国建筑师去给他们设计房子。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不觉得吗?
所有东西合璧这样的话,都是在中国被提出,有可能是中国人提出,也可能是外国人提出,但都是在中国这个环境里提出。我觉得它背后有着很强大的商业目的。如果是一个文化上的愿望的话,那应该是双向的。
我经常被欧洲邀请去什么展览,我就觉得怎么不停地这样,你干脆邀请我设计房子不就挺好?后来我开始有意识去参加一些竞赛。所以现在有两个项目,一个在巴黎,一个在罗马,都会在今年底或是明年开工。
建筑不论是对中国还是对西方,都好像扮演一个文化的角色,所以我是这么看在欧洲的这个机会。我看梦露大厦也会这么看,就是它对北美城市的一个批判。所以一个活、两个活对我并不是很重要,实际的交流就是能把我的作品盖在那个环境里,让那些人能生活在这些建筑里,这是挺关键的。
我希望喜欢我的、或者讨厌我的人,是因为我的作品和我的思想,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或不是中国人。你可以因为中国人这个身份得到文化上的好处,只要承认你是弱势的就可以,因为现在是这么一种状态。但我希望有自己的价值。我不想去贩卖各种身份。在文化界其实已经都很明确,就是贩卖各种中国符号,然后去谄媚西方主流文化。你的价值是因为别人对你有兴趣,觉得你很得到西方的认可,但他并不是真需要你。
跟西方主流文化的这种关系,是一个新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西方得到这个项目、这个身份,不单在中国,在西方也会被认为是一个标签。拿这个事给我当标签,就已经说明一种文化上的不对称。其实有什么不正常的呢?
问:你跟国外建筑师交往时,可以明确感受到你刚才说的这些吗?
马岩松:我是说主流文化,就整体的文化,不是建筑圈。建筑圈是很功利的,他们也喜欢中国建筑师,你以为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项目是怎么得到的,都有人帮忙。
问:谁帮忙?
马岩松:有无数人帮忙。有建筑师,有各种商业公司,有各种人,不知道什么人,反正总有人去帮忙,不然怎么会这么多。你看中国没有建筑师在国外设计房子,我们成了惟一的,这简直是太可笑了。
找我的人往往是叶公好龙
问:找你设计的人,比如说开发商、政府官员,他们是怎么理解你的建筑的?沟通顺利吗?
马岩松:我觉得不同人找我有不同目的吧。有的人是抱着商业目的,觉得你设计的东西能成为标志性建筑。也有那种完成了原始积累,盖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建筑),挣很多钱了,突然想我们今天干嘛呢?然后从了解我们的理念开始,有点带着理想主义甚至赎罪的心情来合作的。
政府呢,有的可能是真喜欢你的作品,也有的是听说中国第一个在国外怎么怎么着,然后带着民族自豪感来找你,但这样的人往往有叶公好龙的结果。
问:结果是什么?
马岩松:就是他觉得你被国际认可了,所以你是中国的骄傲,因为这个原因找你。但我们有我们的理想,对作品要求特别苛刻。很多中国的项目都是粗枝大叶的。你如果不把它当成一个作品,只是一个房子,或者一个产品、一个商品的话,跟我们的要求差得挺远的。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做出这个判断才行。如果你开始没判断对,然后大家都挺激动的,到后边就会很尴尬。
问:你碰过这种情况?
马岩松:碰过。然后会产生问题。这时候就很难受。
问:那怎么办?
马岩松:怎么办也得挺着啦。中国的状态就是大部分建筑师是不用太负责任的,比如说不用管室内设计,施工时也不用去工地,不用管很多像材料的决定。你想管,所有人觉得你是多余的。你的设计费和时间也不允许你干这个,然后你非要管,首先是投入非常大,然后人家还不觉得你是好意,会觉得你管那么多干嘛。
问:你目前碰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或者让你觉得最棘手的?
马岩松:基本上天天在吵架啊。你已经被绑架了,你已经在这条船上了,你只能不停地争取下去。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建筑从开始到最后,不是说我憋一口气就能过去的,六七年的时间,每件事儿、每一天,你都得在那儿顶着,你松一下就一泻千里。
问:你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
马岩松: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而且这个状态还不能成为我的全部,但已经完全够把人烦死了。这就是跟现实斗争嘛。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习惯上是不太愿意这样的。他们是出世的,就是发发牢骚,然后就自己去干别的了,不参与。但我觉得建筑师是一个改革者,像现代派的鼻祖勒·柯布西耶,他写信给墨索里尼说我有一个城市设想,跟纳粹去推行他的理想。他是一个变革者,相信知识分子的行动是有价值的。
问:有种说法是,你跟中国传统印象中比较沉默的、埋头干活的建筑师不太一样。
马岩松:我觉得中国分两种建筑师:一种是做技术,只提供技术服务,这样的建筑师没有个人情感的表达,也没有个人对时代对社会的观点,或者说他的观点跟作品是脱节的。还有一种是对社会对城市有观点的建筑师,但因为看到很多问题,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知识分子这种传统让他觉得要独善其身,不参与进去,所以也就谈不到去改变。
问:也许参与后会被裹挟进去?
马岩松:那就更不能理解了。你如果有自己的立场,怎么会被裹挟进去?在我刚回国头几年,就有很多批评,你发表那么多看法,你倒是盖啊?(笑)我觉得首先我盖不盖,那是时间问题。第二就是即使不盖,光说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一个建筑师一辈子不盖光说,如果你说的东西在点上,也是很有意义的。
西方有这样的建筑师,他就谈理想城市,然后画图描绘出心目中的理想城市是什么,然后发表,大众都看到、讨论。这其实是一个思想的改造者,很多人看到这样的言论和图纸,已经起到一个变革的作用。
中国是连理想都没有人提出来。我觉得改革开放三十几年,这种城市规划上的思想是没有的,根本就没有。所以现在的中国城市怎么产生呢?就全是北美模式,划方格网,一块一块地卖地,没有一个整体的,都是从功能和技术层面。比如说交通,啪,我要开个平安大街,啪,拆一大堆。根本就是很可笑、很无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