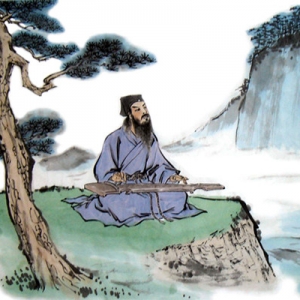摘要:寨山王,黔西北俚语,大致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在当地威望很高,做事出于公心,但手段却有些霸道乃至蛮横。贵州省大方县大山乡光华村的老支书罗光贤就被乡邻送了这么个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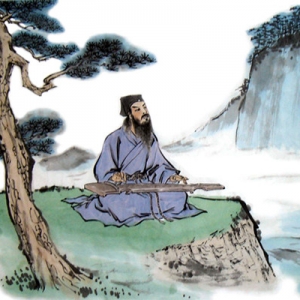
寨山王 罗光贤68岁了,一头白发霜打了一样,村里的事操持了大半辈子,得这绰号不是一时半会儿,全因为平素的行事风格。
就拿今年来说吧,罗光贤带着村民和附近的几家小厂矿杠上了。原来,这几家小厂矿都建在流经光华村的格里河畔,“开工前他们都签了环保责任书,但废渣废水还是都直接排到河里,村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河水污染了,我们哪里还有活路?”罗光贤先是带人到矿上去交涉,无果,一怒之下掐断了他们的用电线路,导致双方剑拔弩张。后来开了窍,到县城找了环保和国土两个部门,小煤窑、小硫黄厂等5家企业全部关停。
打了胜仗的罗光贤并没有闲下来舒一口气,格里河的污染已经到了不得不治的时候。格里河是赤水河上游支流,流经大方县4个乡镇23个村,是当地人不折不扣的母亲河,但由于沿河群众对河流的保护意识淡薄,生活垃圾污染严重,加上大肆捕捞鱼虾,水质严重下降。 
河流污染很严重 “不用提格里河是赤水河的上游,就我们自己吃水、地里种蔬菜瓜果,哪一样离得开这河水?”罗光贤在去年11月份召集了23个村的村支书开会,和大家伙商量怎么才能把格里河管好。
格里河的污染早就成了这23个村子村民的心头病,罗光贤一召集,大家群起响应。当即决定把格里河划分为23段,沿河的这20多个村支书自封“河长”,将河流的管护工作责任分解、落实到人。
会上,大家还一道制定了河流管护的村规民约——禁止以任何方式捕鱼,尤其是使用农药、炸药、电网非法捕鱼的,不光要罚款,还要送交公安机关处理。参会的每个人凑了450块钱,制作了27块大牌子,立在每个村最显眼的位置。
开完会回去,村支书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各家各户摸底,登记所有捕鱼用的电机,一共有20多台。
今年4月份的一天凌晨,正在酣睡的罗光贤突然接到电话说有人在河里用电机打鱼,他从床上跳起来就直奔河边,没收了捕鱼工具不说,还责成当事人负责管护这一公里的河段,直到抓到下一个非法捕鱼的为止。罗光贤提着这台没收来的电机说:“别看这机器小,只有20来斤,两个人配合一晚上就能扫荡2公里的河道。” 
污染后的河流不仅气味难闻 慢慢地,非法捕鱼销声匿迹,村民们看到水质有所好转,也不好意思再往河道里倒生活垃圾了。56岁的杨香贵是村里的五保户,靠着低保过日子,上面来了救济粮油也第一时间发到他手上。“占着村里的低保名额,不做点事心里过意不去。”就这样,杨香贵成了格里河的义务巡逻员和清洁工。现在,杨香贵每天都要沿着村里的河道走几圈,“这个主要是靠自觉,谁家屋后的河里漂了垃圾大家都能看见,难免让人白眼看。”
通过一年多的治理,格里河的水质有了明显好转。原先外出谋生的村民们也纷纷回到老家,搞起了果蔬种植和鱼塘养鱼。“格里河的水养冷水鱼最好,1斤能卖到300—500元,是其他地方比不了的。”32岁的刘国艳今年从云南回来承包了7亩多地搞鱼塘,今年上半年已经赚了7万多块钱。
当然,格里河河谷的优势还不限于种养殖一途。生态环境好了,观光农业、乡村旅游等方面也独具潜力。罗光贤介绍,今年春季,就有遵义的老板来考察,准备在沿河开发桐树种植。格里河生态经济带已初现端倪。 |